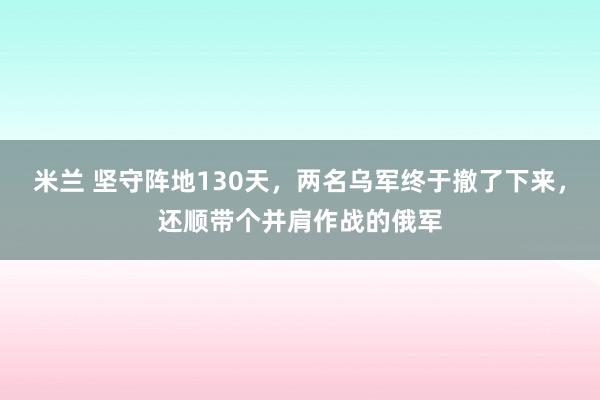

在康斯坦丁尼伏卡方向。德米特罗蜷缩在射击孔后的阴影里,小心翼翼地从防弹衣内袋摸出那张边缘已磨损的照片。照片上,妻子奥克萨娜正抱着三岁的女儿站在向日葵田里,阳光透过塑封表面,在妻子金色的发梢上留下一抹永恒的光晕。
他用指甲轻轻刮去玻璃纸上凝结的水雾,这个动作在过去四个月里已重复了上千次。指腹划过女儿稚嫩的脸庞时,他感到一阵细微而熟悉的刺痛——那是思念,具体而真实。
“第一百三十天。”丹尼斯沙哑的声音从掩体角落传来。他正用烧焦的树枝在混凝土墙面上刻画,炭笔与粗糙墙面摩擦时发出细碎的“沙沙”声。新添的一笔让墙上的正字又完整了一组——五排,每排五个。
德米特罗没有数,他知道从八月初到现在,恰好是二十六组。他点点头,将最后一点温水倒进装着压缩饼干的铁罐,用小勺缓慢搅拌。温水与干粮混合后散发的淡淡麦香,在这个充斥着泥土、铁锈和硝烟味的环境里,竟显得格外珍贵。
爆炸来得毫无征兆。第一声闷响像重锤敲在胸口,紧接着整条战线苏醒过来。“右翼!铁丝网被剪开了!”丹尼斯的吼声被新一轮爆炸声撕碎。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像一场模糊的噩梦,曳光弹在空中织成光网,爆炸的火光将战壕墙壁瞬间染成橙红色。
当枪声骤停,世界陷入诡异的寂静。耳鸣声尖锐地持续着,德米特罗和丹尼斯对视一眼,彼此眼中都是同样的问题。他们是在检查阵地东北角时发现那个俄罗斯士兵的。
他半埋在炸塌的散兵坑边缘,右腿以不自然的角度扭曲,深褐色的血浸透了作战裤。当德米特罗的枪口指向他额头时,士兵睁开了眼睛。那是一双浅褐色的眼睛,瞳孔因疼痛而放大。他盯着距离额头仅三十厘米的枪管,喉结滚动了一下,但没有发出声音。
时间在那一刻变得粘稠。
“他还活着。”德米特罗听到自己的声音,陌生而干涩。
丹尼斯已经蹲下身,拔出匕首割开浸血的裤腿。伤口很深,锯齿状的弹片嵌在血肉里。“需要磺胺粉和绷带。”他头也不抬地说,“最后一包在你那儿。”
德米特罗默默取下背包。当白色药粉撒向伤口时,士兵的身体剧烈抽搐,牙齿死死咬住下唇,直到血珠从咬痕处渗出。他的眼睛一直睁着,盯着战壕上方那片逐渐亮起来的灰色天空。
沉默的共存:战壕里的新规则
最初的几天在警惕的沉默中度过。被俘的士兵——他们后来知道他叫丹尼尔·西切夫——被安置在掩体最深处,双手被塑料扎带松松束缚。语言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,丹尼尔的俄语带着伏尔加格勒的口音,又快又含糊。
第七天下午,一架无人机在阵地上空盘旋了两小时。三人紧贴墙壁,连呼吸都刻意放轻。无人机离开后,丹尼尔用未受伤的腿挪到射击孔边,指着东北方向做了个“绕行”的手势,然后用手掌在空中比划出特定的飞行轨迹。
丹尼斯扬起眉毛:“你在帮我们?”
丹尼尔没有回答,只是捡起树枝在泥地上画简略地形图,标注出几个易遭炮击的位置。他的手指在发抖。德米特罗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,然后从自己的补给里多拿出一块巧克力,放在丹尼尔手边。
那天晚上分罐头时,德米特罗把肉多的那块推了过去。
严寒中的同盟:生死时刻
十一月的严寒让战壕变成冰窖。积水结了冰,踩上去会发出脆裂的声响。他们必须轮流睡觉,因为只要静止超过二十分钟,寒意就会穿透衣物直达骨髓。
一天深夜,轮到丹尼尔值守。德米特罗在浅眠中感觉有人轻碰他的肩膀。他猛地惊醒,手已摸向腰间匕首。
是丹尼尔。他竖起手指贴在唇边,然后指向战壕外的黑暗。月光下,几个黑影正在积雪地带匍匐前进,距离铁丝网已不足五十米。
没有时间说话。德米特罗踢醒丹尼斯,三人迅速各就各位。当第一个黑影接近铁丝网缺口时,德米特罗扣动了扳机。战斗在瞬间爆发。
二十分钟后,枪声停息。丹尼尔放下那挺缴获的PKM机枪,双手微微颤抖。德米特罗意识到,刚才这个俄罗斯士兵完全可以调转枪口——在整个过程中,他和丹尼斯的后背都暴露在他面前。
“你本可以不参与。”事后,德米特罗用生硬的俄语说。
丹尼尔沉默地包扎自己手臂上被弹片擦出的伤口。包扎完毕,他才低声说:“如果他们攻进来……”没有说完,但德米特罗明白了。
雪夜低语:破碎的对话
十二月的雪封住了战线,大规模攻势减少,但炮击仍零星持续。在漫长的等待中,他们开始尝试交谈。
丹尼斯教丹尼尔简单的乌克兰语:“水”——他举起水壶;“食物”——他指着罐头;“冷”——他抱住双臂发抖。作为交换,米兰app官方网站丹尼尔教他们俄军常用的战术手势。
语言像一座缓慢搭建的桥。
一个飘雪的傍晚,德米特罗又在擦拭女儿的照片。丹尼尔看了很久,忽然说:“我妹妹……她叫娜斯佳。”他从贴身口袋掏出一张同样磨损的照片——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的女孩站在伏尔加河畔,“她应该上大学了,如果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只是用手指轻抚照片上妹妹的脸。德米特罗看到这个曾试图杀死自己的人眼中闪过某种熟悉的东西——那是他在镜子里见过无数次的眼神。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将还剩一半的巧克力掰开,递过去一块。
撤离:漫长的三百米
命令是在一月中旬一个阴沉的早晨下达的。无线电里传来带着电流杂音的声音:“天鹅绒-7,准许撤离。重复,准许撤离。”
丹尼斯听完愣了三秒,然后猛地一拳捶在墙壁上。混凝土墙面震落一片灰尘,在射击孔透进的微光中缓缓飘散。
收拾装备只用了十分钟。德米特罗最后环视这个生活了130天的掩体:墙上密密麻麻的正字、发霉的睡袋、用炭笔画在混凝土上的十字架。他的目光在每个细节上停留片刻。
“该走了。”
丹尼尔的腿伤未愈,需要搀扶。三人以古怪的姿势缓慢移动——德米特罗架着丹尼尔的左臂,丹尼斯警戒后方,丹尼尔拖着伤腿。雪地上留下三行深深浅浅的脚印,很快又被飘落的雪花覆盖。
三百米的距离,他们走了近半小时。每一步都可能触发地雷,每一声无人机引擎声都可能带来死亡。德米特罗能感觉到丹尼尔身体的重量,能听到他压抑的喘息。
当看到接应部队的装甲车轮廓时,丹尼斯发出一声介于呜咽和笑声之间的声音。一名中尉迎上来,目光扫过三人时眼睛明显瞪大了——不是因为多了一个俘虏,而是因为这三个人看起来如此相似:同样蓬乱的头发和胡须,同样被泥浆、汗水和血迹浸透得看不出原色的军服,同样深陷的眼窝和异常明亮的眼睛。
移交程序简单得近乎冷漠。两名士兵上前给丹尼尔戴上黑色头套。在被带上车前,丹尼尔忽然停下脚步,转过头。尽管头套遮住了脸,但德米特罗能感觉到他的目光。布料下传来模糊的声音,但德米特罗确信自己听懂了那个词——那个他教过丹尼尔的乌克兰语单词:“谢谢。”
热水:洗净与重生
淋浴帐篷里,当热水第一次冲刷过身体时,德米特罗闭上了眼睛。水流温热而有力,冲走头发里的泥土,冲掉皮肤上板结的污垢。四个月的污垢在脚下汇成黑色的溪流,流过排水孔时发出黏腻的声音。他用力搓洗着手臂,皮肤上留下苍白的指痕——长期穿戴防弹衣留下的印记,像某种无法抹去的烙印。
隔壁隔间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。不是哭声,至少不完全是。那是某种压抑的释放,混合在水流声中几乎听不见。德米特罗没有去打扰,只是继续站着,让热水冲刷每一寸皮肤,直到皮肤变红变烫,直到几乎忘记寒冷是什么感觉。
更衣时,他们站在镜子前。剃须后露出的脸庞瘦削得陌生,颧骨突出,眼窝深陷。但眼睛深处有什么改变了——那种前线士兵特有的空洞眼神,此刻混合着一丝难以名状的释然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帐篷外,新部队正在集结。年轻的面孔,干净的军服,装备整齐得闪闪发光。德米特罗和丹尼斯沉默地看着他们,就像看着四个月前的自己。
中尉走过来递给他们文件:“给你们一周的假。回家看看。”
德米特罗点点头。他会回家,会拥抱妻子和女儿,会睡在柔软的床上。但他知道——他和丹尼斯都知道——一周后会回到这里。不是因为热爱战争,而是因为在那条漫长而泥泞的战线上,有些责任一旦扛起,就只能扛到最后。
夜色渐深时,他们登上前往后方的卡车。引擎启动的轰鸣声中,德米特罗最后看了一眼东方——那片他们坚守了130天的土地正逐渐被黑暗吞噬,只有零星的火光在天际线处闪烁。
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战俘转运站,丹尼尔·西切夫正坐在干净的床铺上,端着一碗热汤。蒸汽模糊了眼镜片。他慢慢喝着,每一口都仔细品味——这是他两个半月来第一次不用担心食物里可能有毒。窗外,冬夜寒冷而清澈,星星出来了,和伏尔加格勒上空的那些并无不同。
他喝完汤,将碗轻轻放在床边,躺了下来。毯子干净而干燥,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。他闭上眼睛,第一次在没有枪炮声的寂静中入睡。在梦中,他仍然在战壕里,仍然和那两个乌克兰士兵在一起,仍然在等待下一个黎明——不知那是即将到来的黎明,还是已经逝去的、再也回不去的黎明。
